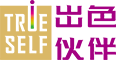联合国新闻:您创办“出色伙伴”的初衷是什么?
阿强:创办出色伙伴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在安徽长大,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始终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性少数充满着很多的挣扎。
当我从学校毕业之后,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焦虑,就是有一天怎么去跟我的父母去说这个事情。所以我就选择去最远的地方,到了广州来工作和生活。这样就规避了我的家人,我们之间有1000多公里的距离。
但即使是在广州工作,当我进入了婚育的年龄之后,父母总是会问,你什么时候会带一个女朋友回来?你什么时候结婚?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内心其实是非常烦躁的,总是不愿意去跟他们交流,逃避跟父母对话。
2006年的时候,我妈妈突然查出了胃癌晚期。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一家人都在医院里面,在病房里面,我妈妈从手术的麻醉里面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我这次死了,我什么都可以放下,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你没有结婚。
这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冲击。我妈妈身体健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跟家人找机会对话或者了解彼此,但是突然之间医生告诉我们她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也许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的时候,我意识到,其实我在跟我自己最重要的人,尤其是父母,扮演另外一个人。
那个时候我非常挣扎:我要不要告诉父母,我现在说出来的话是不是对我妈妈人生最后的这段时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会不会显得我非常自私?后来我妈妈手术之后过了6个月去世了,在她去世之前那段时间,我确实也没有跟她讲。等我妈妈去世之后,我开始真切地意识到,这些挑战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挑战,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我的周围有很多的性少数朋友,他们都面临着这样一个情况。这是当时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出色伙伴提供
2015年来自四川的一对父母在恳谈会上分享完与孩子紧紧拥抱
2008年的时候,我专门把我爸爸叫到广州来,跟我爸爸说了这个事情。然后在2008年的6月份就创办了“出色伙伴”公益机构。
联合国新闻:你感到有非常大的压力,不能够在你妈妈去世之前告诉她,那么仔细分析的话,你害怕什么呢?
阿强: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对同性恋的了解非常少,人们会把性少数或者同性恋看做变态,或者进行污名化。
我的自我认同其实也是非常艰难,就觉得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是一个坏人。当我意识到我自己是同性恋的时候,我会毫无疑问会跟社会上所给同性恋下定义的标签去做对比,我就觉得我怎么能够做那样的人,我不应该做这样的坏人,我不应该做这样的变态,我要去改变我自己,甚至想我有没有机会变成一个异性恋。
这些都是我在成长里面所经历的挣扎,然后我自己从挣扎里面走过来,好不容易能够接纳我自己,认同我自己。但是当我在说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家人,他们可能会经历跟我一样的状态,就会觉得为什么我的孩子是一个不正常的人,或者说为什么孩子是一个变态,或者说他可能会有很多污名化的词语跳出来。我跟我爸爸出柜的时候,我爸爸就说,我很担心你老了怎么办?
所以实际上是多重担忧交织在一起——担心你最重要的人。在中国文化里面,感觉你会让家族蒙羞,让他们丢面子。父母望子成龙,你很担心因为同性恋这个事实让你从所谓的好的这个队伍里面掉下来,掉到一个被人瞧不起、被人贬低或者被人鄙视的队伍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恐惧。
联合国新闻:你父亲除了担心你老年之后的养老的问题之外,其他还有什么担忧吗?还是他很释怀?
阿强:当时我在广州跟他讲了一个多小时,讲了我自己这么多年的人生轨迹,为什么我一定要来到广州,以及我跟我对象之间的关系。
在我跟我爸爸出柜之前,我邀请了很多同性恋朋友来家里吃饭,所以他也跟那些人都认识。然后我出柜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些天来我们家吃饭的这些人他们也都是同性恋。
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觉得这些人也都挺好,不是坏人,所以他从思想上已经认识到这些人都是普通人。
然后我爸就说,我就担心你老了没有人照顾,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就说现在养老也不再是要靠传宗接代,一定要让子女来养老。现在城市里面这些人都是要进到养老院里面去养老,这是一个发展趋势,所以我说你也不用太顾虑这个事情。
讲完这个事情以后,他说,你晚上想吃点什么东西?我去做饭。

出色伙伴提供
出色伙伴家长艺术团在表演走秀
联合国新闻:看到你父亲的反应以后,你是什么感觉呢?
阿强:我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释怀。我说实在话,我犹犹豫豫,忍了这么多年,跟我爸爸出柜的时候,都已经30岁了,从我有这样的意识开始,都已经是20多年的一个秘密了。
讲完了以后对我来说是一个放下的过程。原来我设想了很多,比如说我爸爸会很生气,或者说他很难过,或者是他会觉得这给他一个大石头压在心上,但这些都没有发生,都是我自己的假设。事实上我跟我爸讲完了之后,他也没有放在心里,也就放下了这个事儿。
联合国新闻:一位同性恋者要面对的首先是自我接纳,然后还有社会上的接纳,家人的接纳。在这些不同层次的接纳当中,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阿强:自我的接纳其实是第一的。我从2000年开始参与做志愿者,到2008年创办出色伙伴,差不多已经做了21年社群的工作。我觉得如果一个性少数,自己不接纳他自己的话,那么才是最难过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她的世界是黑暗的,他/她觉得没法活了,会不停地否定自己,无论是在自我的学业,还是在事业发展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一个人自我接纳做得比较好,他/她本身实际上是有能力和有能量去影响家人的,因为父母可能觉得同性恋也是普通人。如果你把工作也做好了,生活也做好了,你自己所绽放出来的阳光的能量,或者说你待人处事的自信心,就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人和你的家人。你的家人就不会觉得因为你是一个同性恋,你就不能够好好工作,你就过不好你的人生。
我爸爸是农村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能够这么快坦然接纳我,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他非常信任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非常努力和积极向上的人。另外我自己所展现出来的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能力,也使他不用去担心这些事。
那么接下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家庭的接纳非常重要。

出色伙伴提供
来自重庆的志愿者小莉妈妈妈在活动中与求助的家长沟通
如果说我们的家人能够接纳,就创造了一个小的空间,可能大环境的改变是漫长的,可能需要很多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小环境的改变可以是很快的。
我们遇到很多家长,在广西、贵阳都遇到过,孩子出柜了以后,他们就把比较紧密的小家族召集在一起在家里吃饭,然后坦诚地讲,我儿子以后就不结婚了,也不需要大家再帮他介绍女朋友了,我儿子是同性恋,以后他就想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讲完了以后,这些亲友们反过来去安慰父母。所以家庭接纳之后,会带来一个巨大的改变。
联合国新闻:从十多年前的情况到现在来看,是一个接纳程度越来越大趋势。现在接纳的程度到底有多大?
阿强:我坦白地讲,也是非常客观地讲,在同性恋的接纳度这个问题上,中国社会其实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发展得非常快,整个社会做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的文化不会通过宗教去打压同性恋,更多的是基于文化、不了解,或者传宗接代、好面子这种文化。
但是这很容易在爱的主题下面跨越过去——因为家长爱自己的孩子。
80年代和90年代这一代人,独生子女比较多,所以父母其实是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他不能说因为不接纳自己的小孩,就可能会失去跟孩子之间的连接,因为孩子可能就不愿意回去了。
所以现在我看到出柜的比例越来越高。十五年前,在广州这种城市,我要去问我身边的人有多少同性恋是出柜的,很多人都觉得怎么可能,我还要去跟一个异性结婚、走到异性婚姻里面把我藏起来。
他们做过调查,2016年的数据是百分之十几的人已经跟自己的家人出柜了。越来越少的同性恋会走到异性婚姻里面去,跟40岁、50岁、60岁那一代相比,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的性少数会比较坚信:我作为一个同性恋,我怎么去跟异性结婚?那不是我想要的一种婚姻。
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了解到原来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他们也是同性恋,他们就是普通人,就带来了整个社会对这个群体的了解也越来越清晰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偏见和歧视也是在大幅减少。
原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家长愿意来站出来说我的小孩是同性恋,十几年前我们要在中国社会里面找一两个人可以接受电视采访,或者说讲讲他们家的情况,几乎都很困难。但是现在在“出色伙伴”,我们有一两千家长志愿者都很乐意去讲他们的故事。家长已经不是觉得说我小孩是一个同性恋是一个羞耻的事情,我要把它藏起来,他可能会觉我的孩子是性少数,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作为家长,我也要去积极地发声,去改善社会环境,让我的孩子生活上变得更加容易一点。
现在很多的同性恋可能跟伴侣在一起生活,像在我小区里面,我的一个好朋友跟伴侣在一起生活已经16年了,都完全是一个公开的状态,另一对也在一起生活了十四、五年,而且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刚刚要了一个小孩,所以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已经是可见度很高的事情。
联合国新闻:你所开展的社群工作是要促进同性恋家庭的和谐,那么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开展这种工作的?
阿强:我们“出色伙伴”的定位是希望通过推动家庭接纳改善亲子关系,让家庭变得更加和谐。性少数群体最担忧、最害怕的就是父母的不理解,父母的不接纳。所以我们就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家长上。
我们有一个热线,2008年开通以来每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30到10:30接听,全年无休,越是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打电话求助的越多。接电话的这些家长他们本身自己都是性少数的家长,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叫同伴支持,他们就很容易引起共情。
另外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分享会,在不同的城市举办这种分享会。因为很多的家长知道自己小孩的情况之后,不敢说出来,担心外人会有一些看法,甚至有一些妈妈不敢跟自己的老公讲,有些老公先知道的,也不敢跟自己的老婆讲。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来去讲述他们家的故事。这些家庭聚在一块来听一听别人家的故事,来看一看就别人家是怎么走过接纳的过程,再看一看别的性少数小孩是怎么规划自己的生活的。
除此之外,我们做了很多的培训。我们现在有2000多名家长志愿者,他们原来可能是求助者,因为参加了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和培训之后,他们变成了助人者,能够帮助别的家庭去改善社会环境,形成一种可持续的非常积极的力量。

出色伙伴提供
刚知道孩子情况的家长与志愿者一起恳谈
联合国新闻:在你们支持过的这么多家庭当中,如果说有一个家庭令你特别难忘,会是哪一个?
阿强:我们原来在重庆有一个家长,她跟女儿之间斗争了很多年,她每次都说是8年抗战啊。
她女儿从小就不愿意穿裙子,母女俩每次出去买衣服都是不欢而散。妈妈总认为女儿不够女性化,所以就要去改变她,以至于把她送去学校训练做空姐。女儿最后也考上了空姐,但她每次化妆的时候,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也就不认真工作,其实是刻意不做了,然后就从这个职位上走了。
她妈妈很生气,家庭就闹得很不愉快,以至于女儿就不回家了,在外面租房子住。但是妈妈间歇性地就要找到女儿单位去。家庭关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然后女儿就说,妈妈你别这样搞,我们家没法过了,要不要你去认识一下别的家庭?或者说我先带你去精神科看一下,如果精神医生说同性恋是病,我们再说。
他们先去了重庆当地的西南医院精神科,医生说同性恋不是病,你们做爸妈的要去改变。我们认识同志的小册子放在医院的精神科,精神科医生就给了他们一本。他们拿了认识同志的小册子以后,就去见了我们重庆的一位妈妈,然后很勉强地跟我们的志愿者妈妈一起去了贵阳去参加我们的恳谈会。
早上的活动结束之后,妈妈在现场就非常地被打动,她说我要是早点参加这种活动就好了,我们家里面也不至于折磨我女儿8年,这8年我把我女儿折磨得够呛。她当时一边分享一边哭……
联合国新闻:你们的组织名字叫“出色伙伴”,有什么含义吗?
阿强:英文叫True Self。我们希望一个人——不仅仅是性少数——可以做真实的自己,而不要去伪装,不要去扮演另外一个人,不要活在一种双重生活里面。我们相信这种真实的力量。如果你现在还不能够去做真实的自己的话,至少也可以一点一点地,今年比去年真实一点,今天比昨天真实一点。
我们不是说要求同性恋比别人做得出色,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更出色的自己,不管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以上是社群组织“出色伙伴”的创办人胡志军(阿强)接受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采访。